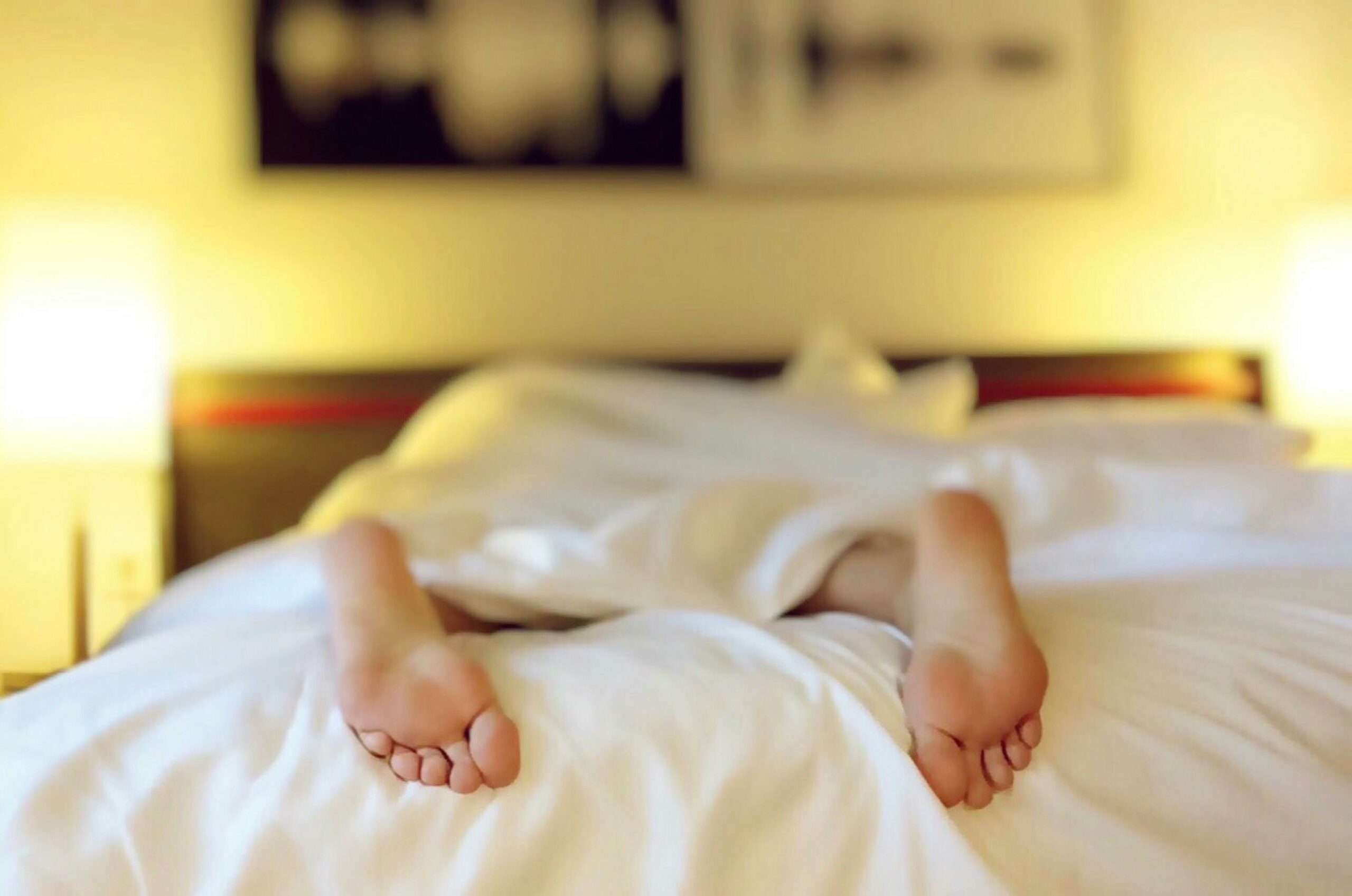访谈:爱丽丝和南希·韦克斯勒
HDBuzz 采访了爱丽丝和南希·韦克斯勒,她们是遗传病基金会的核心人物
遗传病基金会(HDF)是亨廷顿病研究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在 HDF 最近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举行的两年一次的科学会议——“米尔顿·韦克斯勒生命与创造力庆典”上,HDBuzz 会见了南希和爱丽丝·韦克斯勒,她们是 HDF 工作中的杰出姐妹。
韦克斯勒姐妹
HDF 的故事与南希和爱丽丝·韦克斯勒的生活故事交织在一起。

图片来源:爱丽丝·韦克斯勒
1968 年,当她们的父亲米尔顿(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告诉她们,她们的母亲莱昂诺尔被诊断出患有亨廷顿病时,南希 23 岁,爱丽丝 26 岁。和往常一样,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然而,米尔顿不是一个会对此消息坐视不理的人。他找到了民谣歌手伍迪·格思里的妻子玛乔丽·格思里。在伍迪因 HD 去世后,玛乔丽成立了对抗亨廷顿病委员会。
“爸爸一直对研究感兴趣,并希望招募科学家来对亨廷顿病进行研究,”爱丽丝回忆道。
南希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时的科学环境截然不同。“1968 年,没有人听说过亨廷顿病,很少有人对此进行研究。当我们开始寻找对研究感兴趣的人时,很难找到感兴趣的人。”
历史学家和作家爱丽丝补充说,她的关于亨廷顿病的著作包括《走进大海的女人》和《命运的地图》,“实际上,早期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但一个问题是,其中大部分研究旨在识别将要患病的人,以阻止他们生育孩子。”
HDF 的研讨会
米尔顿毫不气馁,成立了遗传病基金会,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并着手对亨廷顿病的看待和研究方式进行重大转变。这仍然是他的女儿们和 HDF 专家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使命。
从哪里开始?让人们交谈。米尔顿利用他作为心理治疗师的背景,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的小型会议,自由地讨论 HD 并交流想法。
HDF 的研讨会——至今仍在继续——总是以 HD 家庭成员向科学家作介绍性演讲开始。“在很多方面,亨廷顿病都是一种非常隐晦的疾病,”南希解释说。“即使是治疗 HD 患者的医生,实际上也不会像对待一个人一样与他们进行一对一的对话。我们认为这至关重要。人们会受到激励,人们会充满激情。”
HDF 研讨会具有独特的规则,以鼓励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它们必须很小,”南希说。“十五到二十人,”爱丽丝补充说。幻灯片和 Powerpoint 演示文稿也被禁止,这使参与者摆脱了舒适区。“每个人都对此感到害怕,但这使人们专注于研究中真正重要的事情,以及数据中重要的事情,”南希说。
HDF 在将一些大人物带入亨廷顿病领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姐妹俩都认为,吸引和支持年轻研究人员一直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找到年轻人,刚开始职业生涯的人,并让他们对亨廷顿病感兴趣,”爱丽丝回忆道。招募年轻研究人员不仅仅是考虑他们未来的年数——他们也摆脱了对如何解决问题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
南希是一位无法抑制的讲故事者,她对一位在早期研讨会上滔滔不绝的高级研究人员进行了深情的模仿:“好吧,这次会议将持续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将获得揭示的真理,然后——什么都不会发生!”但年轻的研究人员没有这种宿命论——正如南希所说,“没有对不可能的事情的认识”。
标记、基因及其他
对不受约束的思考的强调以及利用最聪明的人才为实现看似不可能的目标而努力,创造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 HDF 支持的科学进展。
1983 年发现亨廷顿病的 DNA 标记,以及 1993 年发现 HD 基因本身,都得益于基金会的研讨会、组织和资助。“找到标记是激进的;这绝对改变了地球,”南希开玩笑说——但这离事实不远:DNA 标记集中了对 HD 基因的搜索。从 HD 基因中,我们获得了对 HD 如何造成损害的全部理解,以及我们现在拥有的大量治疗靶点。
除了 HD 之外,“基因猎人”的努力对于我们希望最终能够为包括亨廷顿病在内的许多疾病提供治疗的遗传学革命至关重要。“基因猎人在途中发明了大约十四种技术,”南希说。
南希还是委内瑞拉项目的幕后推手——这是一项为期 32 年的研究,该研究基于该国的一个地区,该地区的 HD 发生率是其他地区的许多倍。来自这些村庄的数百名相关志愿者参与了导致发现标记和基因的研究。来自委内瑞拉项目的 DNA 也被用于发现 CAG 重复序列长度——一个人 HD 基因中的“口吃”次数——会影响一个人可能出现 HD 症状的年龄。
“一个很大的重点是找到年轻人,并让他们对亨廷顿病感兴趣”
自从发现该基因以来,HDF 支持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1996 年,伦敦国王学院的吉尔·贝茨开发了第一个 HD 小鼠模型。贝茨的小鼠被称为“R6/2”,它教会了我们很多关于 HD 突变如何造成损害的知识,并且今天仍然用于研究该疾病和测试可能的治疗方法。贝茨意外地在她的老鼠大脑中发现了蛋白质团块,称为“聚集体”。“没有人认为亨廷顿病有聚集体,”南希回忆说,但在小鼠发现的推动下,这些聚集体很快也被证明是 HD 患者大脑中的一个重要变化。
另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刻是 Ai Yamamoto 在 2000 年进行的研究,她培育了一种 HD 小鼠,其中异常基因可以被人为地“关闭”。令所有人惊讶的是,关闭该基因使已经出现症状的小鼠病情好转。南希特别高兴地回忆起这一突破,因为 HDF 从 Yamamoto 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开始培养她。“我们资助她做研究生工作。她甚至没有博士学位!”她笑着说。
Yamamoto 的工作为基因沉默或降低亨廷顿蛋白的治疗方法铺平了道路,这些治疗方法现在已接近在亨廷顿病中进行测试。2002 年,HDF 举办了第一次关于使用基于 RNA 的药物“关闭”HD 基因的研讨会,HDF 支持的研究人员(如贝弗利·戴维森,我们最近在“EuroBuzz”专题中采访了她)仍然是尽可能快速和安全地将这些治疗方法推进到临床试验的核心人物。
今天和明天
在发现该基因后,为什么亨廷顿病被证明如此难以攻克?“生物学非常复杂;我们非常复杂,我们的细胞非常复杂,”南希解释说。“每次你在石头下寻找亨廷顿基因的作用时,你都会发现一些迷人而有趣的东西,也许是相关的,也许不是。因此,即使弄清楚什么是相关的也很棘手。”
南希挑战了 HD 领域中经常提到的一条传统智慧——我们已经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治愈了小鼠”,现在的问题是“将”这些成功转化为人类患者。“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在模型方面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在小鼠中确实有效的一件事是基因沉默。”
南希认为令人信服的一个成功案例是一种名为 SAHA 的药物,吉尔·贝茨在 2002 年的一项 HDF 支持的研究中首次在 HD 小鼠身上进行了测试。SAHA 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科学的进步对于等待重大突破的人来说会感到如此痛苦地缓慢。
SAHA 被认为可以恢复正常的基因转换,而基因转换在 HD 中会出错。“老鼠的病情好转了。它们提高了握力,并稍微提高了存活率。但 SAHA 有毒。吉尔一生都在研究它的工作原理。”
十年后,贝茨在 HDF 会议上展示了她工作的最新成果,我们在会上见到了韦克斯勒姐妹。“她只是弄清楚了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在细胞中做一些事情——而不是在 DNA 所在的细胞核中。她只是在我们的会议上展示了这一点,十年后。吉尔比我一生中见过的任何人都做更多的工作!”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从一项发现到对它背后的机制有更充分的了解需要多长时间。
因此,考虑到要做的工作量,以及最近在有效治疗亨廷顿病方面取得的进展所带来的乐观情绪,HDF 在不久的将来的重点是什么?“突破界限,”南希以其特有的热情自愿表示。
“我们尽量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爱丽丝补充说,“但也不要到处都是。基因沉默是我们认为值得采取的一种方法。然后是生物标志物的问题——你如何衡量一种潜在的治疗方法是否真的在人类中起作用——这是另一个大问题。我还认为,由于临床试验非常昂贵且难以进行,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坚持在小鼠中正确地完成这项工作”
帮助将尽可能好的治疗方法转移到设计最好的临床试验中也是一个主要重点。“我们举办了很多研讨会,研究如何设计临床试验,”南希说。
HDF 的“蓝天思维”传统在其工作中仍然很明显。基金会两年一次的科学会议(我们在会上见到了韦克斯勒姐妹)在科学家中以展示和讨论令人兴奋的新想法而闻名。除了基因沉默技术和亨廷顿蛋白的化学标记等重要项目外,在会议上展示的 HDF 支持的项目还包括各种各样的研究,例如 HD 小鼠肠道中存在的细菌;快速测量基因转换问题的新方法;在果蝇中研究 HD 基因;以及对细胞进行基因工程改造以产生抗体以防止有害的突变蛋白。
在采访结束时,我们询问未来几年 HD 研究可能会带来什么。“对我来说,这确实感觉像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爱丽丝承认。“但我们不知道。我认为我们仍然面临着乐观和现实之间的平衡。对我来说,保持这种平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我们问及未来十年 HD 研究可能会带来什么时,南希的回答更简短,也更美好。“我会上天堂跳舞,”她说,然后笑了。